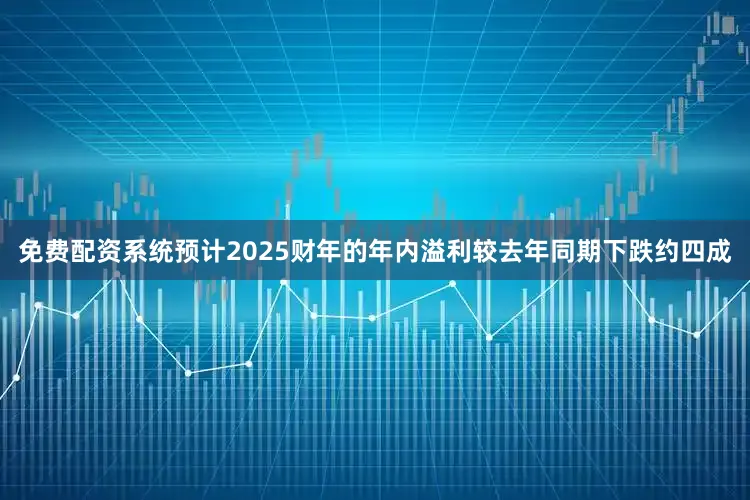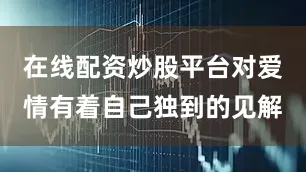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天涯》2025年第4期 新刊上市
点击封面,即可下单
编者按
近年来,《天涯》致力于从自然来稿中挖掘新人新作。通过“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以及“新人工作间”等板块,为更多优秀年轻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天涯》坚信,无论作者名气如何,稿件的质量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些在《天涯》露面的新人,若能持续保持出色的创作势头,未来必定能在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天涯》近两年推出的部分作者,如杨乾、高临阳、章程、杜峤等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
《天涯》2025年第4期“小说”栏目特别策划“新人工作间 2025”,冉也、梁莹、陈煊楠、苏莹、钟芩、李知鸢、苦子这七位从自然来稿里挖掘出来的年轻写作者,展现了他们的宏阔视野和多维体验,其中有三位是第一次发表作品。
我们将陆续推出本期“新人工作间 2025”中七位作者的小说。微信推送这个小辑的小说时,我们还是按照惯例,采取闭环互评的方式,即后一位作者评前一位作者的小说,第一位作者评最后一位作者的小说,形成闭环。
展开剩余95%苦子
“
作者创作谈
替故土流泪
十九岁的那个暑假,我住在黄盖湖镇。我的一位初中老师知道我想写小说,经常找我聊天,跟我讲一些关于小镇的故事,他讲起故事来不怕忌讳,人家家底的事也翻出来讲给我听,包括他自己的家事也不吝啬。后来他给我找来了我们镇的志书,我就看到了黄盖湖镇从1958年一直到如今的历史,沧海桑田。但志书的内容远没有他讲的生动、鲜活、真实。
我想土地应该也会流泪。
那个暑假我经常会听到不合时宜的鞭炮声,这往往意味着有人逝去,外面的老人们会开始探讨炮声来源的那个方向有哪几家人,通过他们的疾病史跟年龄,判断是谁故去。到第二天对完“答案”,去世那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死因就全部清楚。讨论结束之后,我常常看到那些老人叹气、发呆。镇子很小,逝去的人大概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
后来我常常有一个不该有的想法:要是我那位初中老师死了怎么办?那我就听不到那么多的故事了,也无法轻易地了解故土了。那时候我正在学习写小说,我需要故事。
那个暑假结束,我离开小镇时,就感觉怅然若失,好像刚读完一本经典小说还没回到现实里。一直到了2023年,当我开始渐渐忘记那个暑假所听来的故事时,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写这样一篇小说,弄清楚遗忘跟故土的关系,给那些鞭炮声一个交代。
冉也
“
同期作者短评
当遗忘成为必然
——读苦子短篇小说《遗忘转身》
“我”离乡十年后,有了两个月的空闲,以返乡者的视角进入叙事的场域——黄盖湖镇。这个地名本身极具历史色彩,应与赤壁之战中的关键历史人物黄盖有关。当年英雄,大浪淘尽后,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被后人提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历史的前进自然伴随着遗忘与重构,历史上真实的黄盖如何我们无法完全还原,人们真正熟悉的黄盖是小说《三国演义》里的黄盖,那个被后人用文学重新塑造过的小说人物。
作者苦子并未将自己的叙事转向这一历史,而是用碎片式的回忆进入童年、进入当下,以黄盖湖镇为观察对象,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无可避免的“遗忘”宿命。国营农场的历史、百花园的凋零、砖厂衰败消失、方言使用人群的萎缩、老人们的渐次老去……当这些附着集体记忆的地理地标与文化土壤或被改造、或彻底消失,“我”记忆中的故事也变得摇摇欲坠,似乎一阵小风就能轻易吹散。而当“我”尝试调动回忆,以一己之力对抗必然的遗忘结果时,便成了落在纸上的——这篇属于黄盖湖镇的挽歌。
苦子在小说开头就将带有魔幻色彩的意象用来点缀黄盖湖镇的现实生活,用“礼炮”“仙鹤”来标记死亡,又通过镇上居民的只言片语来拼凑成疯子这一人物形象。成疯子是小镇记忆执着的守护者,但他的悲剧性也恰好表明个体对抗遗忘时的绝望。成疯子的“疯”是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的必然结果,就连他的死亡都在一场迅速而模糊的、具有魔幻色彩的葬礼中变得不确切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刘老头的死亡也是用“发着七彩光芒的仙鹤到庙里来接”这样的魔幻情节结束。这种荒诞的死后传闻似乎也成为集体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
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叙述者“我”在归乡后的一番探寻后发现自己也是“遗忘”的参与者。当“我”面对知情者的老去或失忆、面对自己真伪难辨的童年记忆、面对对小镇的过去一无所知的陌生孩童,“我”的叙述显得尤其无力和虚妄。当我再次离乡,听到车窗外炮声又响,我与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对故乡的记忆之绳也愈绷愈紧,“我”便陷入了“绳子崩断”的恐惧之中。
现代化的洪流之下,当维系记忆的空间、载体、传闻被裹挟而去,个体对故乡的遗忘成为或主动、或被动的必然结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遗忘转身
苦子
一
寻常日子,黄盖湖镇除饭点外突兀地响起炮声,一定是宣告有人驾鹤西去。我所乘坐的班车轰鸣,炮声渐稀。没有到站,我就将忘了这炮声。等我再从市里回来,隔壁的骆老婆子点醒我,前天那炮声,把成疯子送走了。
我有了两个月的空闲,千里路途又重归故土。
我所居住的百花园现在看起来崭新,实则败落。骆老婆子是我唯一还认识的人,那些新人家我从未见过,他们看见我时跟我一样错愕,仿佛我闯入了他们的故地。骆老婆子大概很久没有找人说话,我还没进家门,她把我拉住,告诉我,成疯子的事在破庙里办的,是几个基督教徒出的钱,他们信教的人还不错呢。我问,教会不是好多年前就不准搞了吗?她说,他们就是一起办个灵堂,又不聚会,这还算是做好事,其实是政府要他们办的,不然哪个会送成疯子入土?她见四下无人,凑近悄声对我讲,他的灵堂里面,第三天的时候,我的娘啊,好多仙鹤往里面飞,说是有一百只!我诧异不已,不愿相信。还没质问她,她说,我反正没看到,那些教会的人都看到了,仙鹤一排一排飞来,一列一列飞走。我说,奶奶您莫要说些鬼话,您是从哪里听来的?她说,我搞忘记了。我说,哎呀,别人骗您的,您还以为是真的吧?现在野鸡都冒得,还仙鹤!她一边躲开一边说,反正有这回事,反正有这回事。
我当然不相信这些鬼话。我赶到小庙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封条又重新被贴好,比大门上的挽联要新。门缝里透出邈远的奇楠香,似乎又梵音依旧,我看进去,想不到小庙外面破旧不堪,里面的佛像却干干净净,鲜艳生动。我找到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口径全都一致,说一百只仙鹤一排一排来,一列一列走,一只一只的,谁也数得清。我才不信他们所说。我找到以前学校的老师,他的毛发跟我今天买的盐一样白,我问他,老师,成疯子的灵堂里,真有仙鹤飞进去?我想唯物主义者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他说,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哪来的仙鹤?我心里偷乐。他又说,是一百只天鹅,就是黄盖湖滩涂上面的那种天鹅,不对,我记得最后一排少了一只,是九十九只。我头皮刺痒,乱搔,把头发抓得像疯子,我问,您看到了?他说,我冒赶上——我心里又清晰起来——我只看到了最后的九只。我问,您说的真话还是假话?他一愣,我不记得了,我搞不清楚了,我忘记了。我料定他已经糊涂,我当年离开的时候,他正在糊涂的边缘。
那个时候镇里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现在这些老人已经记不得上午是晴还是有雨,留守儿童也早已离开。我总不能去找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外来小孩子问个明白。我离开的时候镇子里还有不少中年人,现在却连一头半乌黑的头发都找不到。
晚饭后我沿界河散步,天色昏暗时,我看到水面上有东西浮起来,是好多半截坟墓,数不清的残疾的天鹅在上空哀鸣、盘旋,苟延残喘。
二
近来几日,我常在门口的摇椅上发呆,像过去已经油尽灯枯的老人一样。过去花草树木葳蕤的园圃现在是一片空地,铺满不会说话的石板,钉着老年人活动器材。曾经缠绕在杉树间使它们受苦受难的钢丝现在变成了各家的不锈钢晾衣架。时间把人的关系斩得干净。
我离乡十多年,已沧海桑田,却又是一种没有外貌改动的巨大变迁,像没有变动的复杂雕塑贴满了灰尘污垢。我走时,园子里的老人们和花草已经油尽灯枯,似乎镇上的老人们也已经油尽灯枯。
对门的小孩在玩健身器材,我把他叫到身边,问:你爸爸叫什么?
他说出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我一怔,又问: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他说出我熟悉的名字,并且补充,我爷爷已经死了。我没有话了,又跟他聊。
你知道砖瓦厂的烟囱是怎样倒的吗?我问。
什么砖瓦厂?他问。
砖——瓦——厂——我加大声音。
什么砖瓦厂?他问。
就是那边,我指着河对面,那边叫砖瓦厂。
他对着天看了片刻,问我:烟囱呢?
我摆摆手要他回家,冷冷告诉他没有烟囱。他刚走动,我叫住他,成疯子你晓得是哪个吧?他答,我不知道。我摆手。他完全对黄盖湖镇一无所知。
砖瓦厂的烟囱是前几年建设美丽乡村时被炸掉的,因污染环境。那时候我在外面,同乡人录了爆破的视频发在老乡群里。爆破之前有人采访成疯子,问他的感想如何。成疯子对着镜头罔知所措,两条泪水死死缝在脸上,大风吹不动。他说这根烟囱是黄盖湖农场的神,要尊敬它,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黄盖湖镇!砖瓦厂可以不用,但是不该炸!他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不舍。视频里猛地一声爆炸,烟囱溃散坠落,顶部砖块落地时,我看到泪水纵横交错爬满了成疯子整张脸,随即像藤蔓一般缠绕了他的整个身体。下面的留言全都在笑话成疯子,说他好笑,说他还是疯。
三
我记忆里与成疯子有过一次交集,在我的小学。那时候他头脑清不清醒,我不知道,总之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非常厌恶害怕他,我奶奶过去告诉我,成疯子是个极其好色的人,喜欢偷女人的内裤塞进裤裆里。她告诫我,我一个人遇到成疯子了一定要跑,跑不掉了要大声喊救命,被他抓到了就不得了了。在学校里,我们女同学传出关于成疯子的流言,说成疯子是色魔,已经糟蹋了两个女学生了。老师也告诉我们女同学,不要跟成疯子有来往。那天中午,我去上学,他诡异地从路边的小路蹿出,对我发出奇怪的笑声。他身上臭,蓬头垢面,头发像被野狗撕咬过。我拔腿就跑,他一把攥住我的衣服,我听到锐利、窒息的布匹撕裂声。他对我说,小孩,给你。他的手打开,是一颗崭新的棒棒糖,我不敢动,他松开我的衣服,打开我的手,将糖放入我的手心,笑着离开。等我从恐惧中反应出来,他已走出十几步。我狠狠将糖扔出去,正中他后脑勺,我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蒙了,苦着脸去捡糖,我撒腿就跑。
这是我记得的事,我不记得的是他什么时候变得正常。我在门口摇椅上和花草一起发了几天呆,循环地在小半辈子的残缺的回忆里搜索、撷取,从没有了名字没有了模样的人的嘴里拼凑出了一小段故事。早些时候,成疯子还是疯子。他依旧在深夜里在睡前去翻垃圾桶,正逢接连几日有人办席面,他捡了好几瓶有剩的酒,不就菜,一口一瓶全部干完了。摇晃着身子回到桥洞底下歇息,他躺在几大坨烂棉花上,来去睡不着,像有火焰在他血液里沸腾。桥上有两个刚刚喝了酒的流氓,是镇上有名的文哥和武哥。他们俩趴在桥上呕吐,呕吐物像两条布落下。他们吐完了,成疯子被这股带着酸味的肉香吸引,他爬起来准备接呕吐物尝尝味道。文哥说,卵子,喝了酒浑身有劲,有劲冒得地方用。武哥说,搞个女人我们哥两个玩哈?文哥答,那有什么意思。武哥问,那去搞点什么事?文哥答,他个婊子,杀个人玩?武哥恐,杀——杀哪个?文哥吐了两口,说,走!就去找那个成疯子,捉到了就把他打死算了——不行,就把他按在河里淹死算了。武哥应,可以!搞得!反正他是疯子,死了就死了,没得用,找他去。
成疯子一下听懂了这几句,吓得酒醒,抖着身子匍匐着往旁边菜地里爬,在菜叶中隐匿。文哥、武哥真下到桥洞里,一阵找,一阵踢,踢垮了挡风的烂木板,踢飞了成疯子捆好的垃圾,踢破了成疯子的粪桶,粪水溅了文哥、武哥一身,固状物抛进了他们嘴里。武哥怒骂,他个婊子养的,老子捉到成畜牲了非要打死他个臭狗日的。文哥怒骂,狗日的,今天就在这里等他一夜,老子看他回不回来,捉到他了老子要把他卵子都给剁了!成疯子吓得不敢动,但浑身发抖,夜里风大。有条手腕粗的蛇从他身上爬过,他就一动不动了,那条蛇最后缠在他的脖颈,一直收缩、蜷曲。
第二天,镇上人都说他更加疯了,他逢人就问,我知道我姓成!可我从哪里来?可我从哪里来?
四
终日在摇椅上,我无聊至极,就把对门的小孩叫到跟前逗他,你不晓得成疯子是哪个?他摇头。我把我知道的关于成疯子的所有事讲给他听。他问我,成疯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摇头。他再问,那成疯子到底是不是疯子呢?我告诉他,过去我不知道,后来应该不是。他问,之前你为什么不知道?他一直在问,我万万想不到他一个小孩对成疯子竟如此感兴趣,我牙关紧闭,使劲摇头,摇椅也一直摇动,无数的小石粒被压得粉碎,声音传入我耳朵里爬,瘙痒难忍。
砖瓦厂被推平之后荒成了泥巴地。清理破砖烂瓦时有六辆渣土车,成疯子循环地拦住等待装车的司机,问,你们运到哪里去?还送不送回来?他也循环地对镇上看热闹的人赞叹,这多好的砖,这多漂亮的砖呵!那些外地司机说成疯子脑子有问题,镇里人又觉得他傻掉了。有人打趣他,成疯子是有心,舍不得他的根哩。有人对他开玩笑,成疯子你要是舍不得这些红砖,你趁现在还没有清理干净,赶快偷一些回去!成疯子找到雇他守鱼塘的老板商量,刘老板,我求您一件事,我想去砖瓦厂搬点砖头瓦片堆在您屋的外面,不会占您的院子。刘老板手一挥,你还没麻烦过我一桩事嘞,只要你不丢到我的塘里,随你怎么放。等成疯子赶到砖瓦厂,好砖瓦已经被运走了,只剩苟延残喘的残砖废瓦。他靠双手一趟一趟把这些碎烂、锋利的东西往守塘的小屋搬。有人劝他,成疯子你去找刘老板借个板车嘛,这样怎么搬得好。他说,不麻烦,是我多来回几趟的事。那人见成疯子不按自己意见来,留下一句死疯子。成疯子把残砖烂瓦垒成墙,一面一面的靠着小屋外墙垒了九层,有半个小屋大。刘老板提醒他,成疯子你小心哦,这些砖头要是把屋压塌了就不得了了,你小心点!
我暂时又无法找寻到关于成疯子的记忆碎片了,这些隐秘的回忆就如同被烂砖瓦死死覆盖住的那面屋外墙一般,再难重见天日;或者在以后,屋外墙也随着破烂砖瓦一起坍塌、湮灭,一切都从未存在。
摇椅一直在摇,两只木摇脚把水泥地碾出深深的伤痕。随风摇晃时,如镇里人剁辣椒的两把铁菜刀,响不停。
一片枯黄的树叶落到木摇脚下,瞬间就破碎,来回几次,犹如人死后烧成灰的衣裳。我又记起一些往事。我的初中,约莫过去二十年,只叹黄盖湖镇没有留住我,现在我不愿与故土割舍了,其实又是叹我的无能为力。初二,镇里面启动危房改造计划,成疯子加入了镇政府的施工队。这是政府给他的关怀,一开始政府决定按半个小工付他薪酬,他坚决不要,说,拿了钱就是我麻烦你们了,我不麻烦你们。那些人白眼一翻,暗骂,傻!成疯子干活一人抵两个泥瓦小工,劲大,蛮干。跟他一起的小工有大把时间闲聊。
之后的美丽乡村建设,百花园改造——园子中间恣意盎然的园圃被推平,换成了简单的石板走道。推土机推了一整天,园圃里了无生机,泥土被蹂躏得不成样子,昆虫残损的尸体遍布;花草七零八落地堆在一边,它们根茎折断处的汁液已不再流动,偶有苍蝇停留。只有成疯子觉得这是惨状,他向园里的住户们叹息,百花园以前是农场老干部宿舍,现在没干部了,这一小片泥巴以后也看不到了,哎。园子里的人骂他,成疯子真疯,有毛病,狗儿猫儿死了他也要去伤阵子心,念念咒,总喜欢搞这么一套。
五
我在摇椅上摇了许多天,摇不出一丁点儿破碎记忆和想象,于是决定出门。镇上的公墓是前些年新修的,里面有好多我认识的老人,或许还有一些人的墓碑在架子山上散落,或者不知道在哪里。今天墓园还没开始打扫,满园的枯枝败叶一直飘舞。走到我奶奶的墓前,我陡然感到过去的光景像针线一样往我身体里反复穿插,把我缝成茧。我跪在反复被灼烧的肮脏的石板上,双手抵着我奶奶的墓碑,我的心仿佛被放在干透了又没刮干净的滚筒水泥搅拌机里一直翻炒,内壁上怪异嶙峋的突起水泥块时时刻刻处处刺拉、划剖着我的心。百花园的园圃也是被水泥搅拌机吐出的泥流给掩埋,那些难以重见天日的泥土与我一同流泪。
我走了许多地方,渐渐把一些将要遗忘、已经遗忘的土地与记忆一一相对,整个黄盖湖镇的版图,清晰明了。眼皮下垂只能靠透明胶布提拉眼皮的老人的嘴;中风之后只能靠助行器移动的老人的眼;瞎了一辈子却没有走过歪路的老人的耳;头发雪白的退休教师的所有感官。这现实、飘渺的一切又重新为我演绎一段往事。
是千禧年的事。成疯子清白之后不敢再回桥洞,不敢与文哥、武哥打照面,文哥、武哥清醒之后也不敢与成疯子见面。成疯子没清白之前,夜里翻各个垃圾堆,他的脑子里,只要物件脱了手,入了垃圾堆,那就是他的东西。文哥还没跟武哥厮混在一起时,曾经扔过一件破衬衣,等他发觉口袋里留了十块钱的时候,成疯子已经穿在身上了。文哥说,你个狗东西手脚还蛮快,老子衣服里面还有十块钱,拿出来给老子。成疯子不理他,文哥骂,你妈个×,老子给了你脸吧!一脚把成疯子踢进了垃圾堆里,上去扯衣服。成疯子把衣领一拉,身子一弹,打两个滚滚开,拔腿就跑。文哥边骂边追。快追到砖瓦厂的时候,路上许多细小碎砖,文哥边追边捡砖头砸,一块鸡蛋大的石头精准命中成疯子后脑勺,成疯子刚刚捡的玻璃杯破碎坠地。文哥一惊,以为脑袋破了是这样的声音。成疯子回头看一眼文哥,又跑。文哥又砸又追。跑进砖瓦厂,成疯子看文哥还紧追,把砖瓦厂里垒起的好砖好瓦拿起来对着文哥砸,边砸边嚎,文哥不退也不近,一直闪躲。等好一批砖瓦都摔碎后,文哥叫来了砖瓦厂的管事人。管事的看成疯子摔坏了那么多砖瓦,手一挥叫几个汉子用麻绳把成疯子捆在一棵大樟树上。他们问成疯子为什么糟蹋砖瓦,成疯子不作声,不管怎样问,成疯子就是乱嚎乱叫。管事人说,你个死疯子,狗东西,捆他两天给他长点记性。人都走后,文哥上去骂成疯子,你个勺婊子,你再跟老子狠一个看看?老子怕你个疯子?他上去一顿拳脚,又翻他的衬衫,翻遍了口袋,没有找到半毛钱。文哥见到成疯子狰狞地瞪着自己,忽然心悸,对成疯子狠狠地踹了几脚,成疯子开始狂嚎,把厂里的狼狗都吓得低呜绕开。文哥怒甩了一巴掌,在他的衣服的干净处揩干净手,留了几口痰和一句畜牲东西!
成疯子清白之后,觉得砖瓦厂是去处,是归宿。没有求人,没有找事,成疯子到厂里只在后面帮拉砖的工人们推车,推了两天车,工人们渐渐让他帮着拉。谁要方便时,招呼一声,成疯子就上,不管是卸窑砖还是入库砖,他都摆得整齐。一人高、两手长的砖堆,他堆了三个,人家才刚刚堆完一个。后面不只是三急,谁想要歇息了,只需挥手招呼成疯子。劲大,不惜力,是所有职工对他的评价。他们的乐子是坐上斗车让成疯子拉,人人都说成疯子拉得比马快。他们茶余饭后议论成疯子:总还是个疯子!在厂里帮了个把月忙,厂长和农场书记注意到他了,书记看他脑子恢复正常,一声令下:暂时让成疯子帮忙拉砖,管吃不管住,看后续表现。成疯子半个身子,就落到了黄盖湖镇。此时,他大概已走过小半辈子。
饭后,我打断玩遥控飞机的小孩,给他讲了这段故事。他抱着飞机渴望地问我,然后呢?我没有话了,支支吾吾说,后来,后来我也不大记得了,等我找……等我问……等我想,等我想起来了再告诉你。小孩有些失望,随即眼睛闪着光把他的遥控飞机和遥控器一齐递给我,说,姐姐,你玩不玩,我给你玩。我摆摆手。我不会玩。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玩过这新奇玩意,在我的童年,也没见过这新奇玩意。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会打珠子、钓龙虾,到界河边上捏泥巴。
六
我花了半个月时间,走遍了黄盖湖镇的每一条路。有些小径让我迷茫,在半途,荒芜、恐怖,我不知道通向哪儿。我会认为这路是新踩出来的,我的脑子毫无印象。有一处田埂让我记忆重置,成片的没有界限的绿色麦田与天衔接,我似乎被玻璃罩给盖住。辽阔的麦田让我压抑、眩晕。麦苗似波浪起伏,我的身体浸在风里。成疯子守过的鱼塘已是野塘,旁边的小屋坍塌,一堆破砖烂瓦。
架子山上刚刚废弃的小庙,也愈发破败不堪,成疯子走后,无人管理。这段事是谁告诉我的?我记不清了,半个月里我向许多老人都打听过,那些老人牙齿都掉光,舌头也萎缩,讲到激动处,口水如雨飞,扁桃体一览无余。
成疯子在砖瓦厂有了活干,仍旧每天翻垃圾堆。寒冬腊月里,他翻得更加迅速、着迷。那时候镇上熏腊肉是三根木棍子一架,毛毡一盖,支起一个三棱锥体的小棚,燃起枝叶就一天一夜地熏。老卢家腊肉隔垃圾堆不远。那天夜里,守肉的老卢迷糊着打盹,他下午去聚会了,在长凳上抱着《圣经》跟着其他人念到了吃夜饭,他不识字,只会说,阿门,阿门,啊地鹿鸭。每到这几句祷告词时,他就挺起胸膛,声音盖过所有人。成疯子在翻垃圾。两个黑衣人摸到熏腊肉小棚子前,麻溜地割掉绳子,顺走了所有腊肉。他们点燃棚子之后,从翻垃圾的成疯子背后离开。成疯子翻完垃圾回头时,在脚底捡了一根腊肠。熏腊肉的小棚烧散了架,木棍子摔在地上,把老卢吓得跳起。老卢赶忙拿盖的破棉被扑火,捡起棍子拨开灰烬和火星子,他找不到一丁点腊肉的影子。犯疑时,望见了成疯子。他跑上去擒住成疯子,恰好摸到了成疯子手里的腊肠,心落了地,立马招呼一屋人出门,来人!来人!婆婆快起来,卢卢快起来!有偷腊肉的!老卢一家子把成疯子围在熏腊肉的小火堆旁,堆中火星依旧。成疯子说,我没有偷腊肉,我真的没有偷腊肉。老卢的儿子小卢上去就重重地给了一巴掌,骂,你个婊子养的,抓到现行的了,还说不是你,不是你,难道是老子偷的?你给老子把肉交出来!小卢夺过成疯子手里的腊肠,一闻,对成疯子说,这就是我屋熏的腊肠,你个狗日好大的胆子,偷到老子屋来了!老卢说,他个狗日他偷了肉还把我们的棚子烧了。小卢一鞭腿甩到成疯子身上,骂,你自觉给老子把肉拿出来!成疯子有点怏了,说,我没有偷你们屋的腊肉,我没有偷,这腊肠是我在垃圾堆那里捡的。小卢又是一鞭腿,成疯子扑地。小卢骂,你还跟老子说得巧,你捡的?是不是腊肠长了脚自己跑到垃圾堆里跳到你手上让你捡的!成疯子在地上嚎叫,像上了案板受了放血那一刀的年猪。老卢对成疯子说,你也莫要在这里鬼嚎,把腊肉还回来,就算了,明天也不把你交到农场去。小卢又一脚踢得成疯子一阵嚎叫。小卢对老卢说,莫跟他啰嗦。又对成疯子说,你自觉给老子把肉拿出来,莫要老子去找,老子要是找到了你今天莫想走着回去,老子不搞走你半条命老子就跟你姓!成疯子缓了片刻,说,我是真的没有偷你们的腊肉,我没有偷哇——我没偷啊——小卢踩在成疯子身上,吼,你只管跟老子犟,你看老子今天治不治得了你。小卢反擒着成疯子双手,两膝死死抵着成疯子的屁股跟腰,开口招呼老卢跟卢婆去垃圾堆里找肉。老卢的小孙子揉着眼睛探到门外,走到小卢面前,问,爸爸,这是干什么?小卢说,卢仔仔快回去,这是个扒手,他偷了我们屋腊肉。小孙子说,这是个坏东西。小卢说,是的,你快点回去睡觉。小孙子对成疯子吐了几口唾液,骂,死偷子。小卢催他回去,小孙子说要尿尿。小卢让他到门口去尿,尿了赶紧回去睡觉。小孙子不肯,说要尿在小偷的头上,说着拉下了裤裆。小卢双手双脚都使着劲,阻止不了儿子。童子尿淋在成疯子脸上,他像被七八个大汉按着放血的猪一样,发起生命中最后的冲锋,猛地大声怒嚎,猛地两个打挺,打滚,把小卢掀翻,把小孙子吓哭。成疯子对还未爬起来的小卢吼,我没偷肉!拔腿就跑,没有十步,又被小卢擒住了,小卢狠狠地掐着成疯子的手筋,疼得成疯子呜呜乱叫。小卢喊老卢跟卢婆,让他们拿麻绳来。他们把成疯子手脚捆死,又把整个身子缠一遍,像要送去宰杀的猪一样。一直到天亮,老卢一家也只找到了那根有成疯子牙印的腊肠。
成疯子呜咽了半夜,第二天的样子与他疯乱时一模一样。老卢一家怏在门前,小卢打了半夜,无力瘫坐;成疯子受了一夜打,说了一夜没偷肉。等人在成疯子周围聚集成众,老卢跟卢婆又有劲了,卢婆坐在地上边哭边怒,老卢在给大伙们讲成疯子偷肉的手法和经过。当老卢得出腊肉被成疯子藏到远处结论时,小卢也有劲了,他说,这个婊子养的也算是砖瓦厂的职工,把他拖到砖瓦厂去,要厂里出钱赔肉。成疯子又爆发,在地上蜷曲打滚,他红着眼对所有人歇斯底里吼道,我没有偷肉,肠是我捡的……无人理会他。他对老卢一家人再吼:姓卢的——老子要是偷了你们的肉,老子把头剁下来给你姓卢的一屋!
后来庙里管事的刘老头到砖瓦厂里准备买砖扩建庙,见到了被捆了两天的成疯子,用化来的钱赔了肉,把成疯子领到庙里。成疯子说,我没有偷肉。刘老头说,你晓得,我不晓得,农场里没有人晓得。刘老头望着佛像,说,他们晓得。小成,你以后下了工到河里洗个澡,洗得干净了,再来跟我把这庙跟庙里的佛像都擦干净。擦完了,你想走就走,该翻垃圾就翻垃圾。
送刘老头西去的炮声响起的前一夜,刘老头告诉成疯子,小成,你记下我这一句,不给任何人添一桩麻烦……刘老头彻底西去的那夜,成疯子看到有发着七彩光芒的仙鹤到庙里来接刘老头,把一切照得透亮,然后消逝。
七
我把这段故事跟对门的小孩讲完,镇上又响起鞭炮声,我的脑子一阵抽痛,感觉里面有东西蒸发。小孩哀求我,让我今天就把成疯子的所有事都告诉他。我说,那不行。他说,你再不说,我就听不到了。我问,为什么听不到?他说,暑假完了,我要回浙江上学了。我沉默良久,说,我也跟你讲句实话,我不晓得,成疯子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是疯子我也不晓得。或许后面我会晓得一些,可你不会晓得了。他说,明年你会不会知道?明年暑假我还到这里来玩。我说,我不晓得,或许,我不再回来了。
第二天,他的父母往车上装行李时,他到摇椅前,递给我一个他的作业本。他说,姐姐,您可以把成疯子的事写在这个本子上面吗?写好了您就放在我家的窗台上。他指着他家,那个是我家,我爸爸说了,每年暑假我都会到乡里玩,明年我一定会看到。
小孩真是纯洁,天真又可爱。
小孩走后,我愈发强烈地想要寻找到成疯子那段最隐蔽、破碎的往事。
近来,每隔几天就会响起炮声,一打听,竟全是老了人。之后炮一响,我就感觉有记忆被炸碎,不复存在。隔得近的声音,我能听完整个过程,先是急促、浓密的鞭声,炮声需细听,鞭响结束,只剩炮声依旧,一响隔数秒再响,竟有余音绕梁之感。最后,像是死亡真正的倒数,炮声一响,去世的人的魂就淡一分。最终一响止,那魂魄也化粉远飞。
我沿镇子的街道一圈一圈地走,年轻的孩子们竟都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玩闹,在生气,在任何时候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如此,黄盖湖镇方言岂不是要被淡忘?无妨,镇子还没转镇之前是国有农场,初期的人,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各个地方,半个世纪走过,方言已是四不像。这四不像的语言,也只有镇子的几千人使用,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使用。这样的语言,或许被遗忘也不可惜。我再没有找到了解成疯子的人,或许小庙的菩萨知道,可他们不会跟我讲话。炮声隔几天还是有响,我意识到,只有这些人知道,可是炮声一响,成疯子的故事就缺少一段;炮一响,小镇的记忆就少一片。
我在探寻小镇往事的梦里,无数的冲天响炮一圈一圈、一层一层把我包围。刺眼的火光一亮,我的瞳孔缩到消失。炮齐齐向我发射,在我身上爆炸,在我的皮肤上灼烧。我的皮囊如蜡一般流走,火烧入我的骨髓里。我被炸得黑烟滚滚,只剩灵魂。我的记忆,尽数被炸得粉碎,不再存在。
假期结束,我也要回某个海滨城市继续工作。清理行李时,对门小孩给我的作业本无意跌落。在离别的前夜,我摊开他的作业本,向隔壁左右借了笔,欲送对门的小孩一个完整故事。
八
小朋友,你好呀,现在我向人打听到了成疯子的事情。写给你看,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得到。成疯子或许是北方人,他生下来时或许也不是傻子。三岁的时候,在村里发烧,家里人没有送到县城医院,在村里找了神婆用了偏方,这时候家里人不知道他是傻子。五岁时他只会说一些简单的叠词,家里人开始慌了,又找到神婆,神婆把黑的、黄的各种符水往他嘴里一顿喂,喂得他哇哇哭。这一治似乎变得更傻了。同村淘气顽皮的孩子要他喊爹他就喊爹,喊得欢快又激动;要他学狗爬,他就学狗爬;要他像狗一样吃屎,他就像狗一样吃屎。成疯子他父亲每次把他提起来往家门口一甩就怒骂,你真连畜生都不如啊你!他父亲与他母亲商量把他带到外面扔了算了,他妈不做声,使劲揩眼泪,揩不动了才开始哀嚎。隔壁左右来劝他父亲,莫要到外面丢了,可惜,养大了傻归傻,也总能抵些力气用。他父亲觉得有理,他母亲这时已经跪在了家里的泥菩萨下。一直养到了十五岁,他什么农活也学不会,翻田把泥往人家地里扔;插秧全是倒插;除草净拔苗;会扒一点玉米,扒了就往嘴里送。活一点不会干,吃得比牛多。他父亲的底线断了,决定要把成疯子扔了。他母亲不说话,揩眼泪揩得脸破皮冒血,他父亲一巴掌打得他母亲转了几个大圈。
他母亲进行着长久的无声无动作的抵抗,他父亲就只能对成疯子嫌弃辱骂。后来某一天,他父亲欣然赶回家告诉他母亲,他在湖北某地找到了一位良医,准能治好成疯子的病。成疯子走进来,他父亲目光流转变化,他母亲悲欣交错。他母亲掐着手指想了半晌,哀求他父亲,说,别治了,治不好又浪费钱,就这样过下去,过下去——他父亲牙一咬眼一瞪,说,必须去,去了就治好了。
一家人打好包袱,到了湖北蒲圻县城,下车他母亲问,怎么到这一小城来,医生在这里吗?他父亲淡漠地告诉她,是,莫瞎问。在城里找了三天,一家人没有见到穿着白褂子的良医,倒是见了几个算命先生,算命的算出两个字:迷,乱。他母亲想等后续的解答,他父亲拉着他们就走。第四天,他父亲给他母亲买了返程票,郑重告诉他母亲,我们的钱不能耗在这上面,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吃,你先回去,我带着他继续找医生。他母亲噙着泪想留下,被他父亲强扯到月台上,他母亲要上车时,他父亲几乎把全部钱给他母亲,他母亲不要,又递回去,说留给成疯子治病。他父亲在嘈杂声里趁着他母亲目无定处时偷偷把钱塞入了她随身的包袱里。他母亲还是不愿走,无声的眼泪从她眼角涌出,如雨水洒在成疯子身上。他父亲想动手打他母亲,月台人多,只是怒骂、推搡。母亲与成疯子拥抱过后,被父亲逼上了车。
母亲一路上像死一般,眼泪浸透了大袄。到家,他母亲在泥菩萨前久跪不起,两天茶饭不进,直到他父亲一个人回来。等他父亲发现他们家一分钱也没有了时,他母亲睁开眼,任由他父亲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她,打得双脸肿胀,牙关不合。
成疯子在车站里不断被肩膀撞击,上身摇摇晃晃,双脚一动不动。屎尿从他的裤腿里流出,他就站得四平八稳。人流把他带出车站,千番波折,一路上,是春夏秋冬。在某个夏夜,月光亮得如太阳,照亮了每株稻穗下面的一只只稻飞虱,万物静谧却又生机勃发。月亮牵着他,引到了黄盖湖镇。
九
我的楷书写得极差,到了半夜,我才写完这些。我这一整晚都辗转未眠,害怕,又怅然若失。第二天,我把作业本放在塑料袋里紧紧地系在了小孩家窗户防盗网上。风一吹,袋子簌簌响。
我踏上离乡的班车,炮声又响,我感到我的心脏有无数根莫名其妙的弹力绳与故地相连。炮声愈淡,绷得愈紧。我万般酸楚地祈祷炮声停止,祈祷此后没有炮声,一是怕绳子崩断,炸碎我的心;二是怕故土再无记忆,全是遗忘。我在车上昏昏欲睡,跟着颠簸迷糊地摇头晃脑,路两边深邃隐秘的林子里探出无数冲天雷的纸炮管,它们一起开火,把班车炸得粉碎。
作者简介
苦子,生于2002年,现居湖北赤壁。此为作者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发布于:海南省融胜配资-广西股票配资-168股票配资平台-正规的配资炒股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